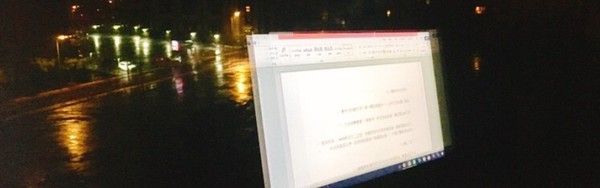掃墓變鬼放火!「帶火金紙亂飄」=鬼搶錢不能掃 清明每日釀百多件火災
老奶奶說當時他們一家人在燒紙錢,燒到一半一陣陰風吹了過來,把好幾張帶火的紙錢吹向空中飄。老奶奶表示那是「孤魂野鬼在搶錢」千萬不能去打擾…

噁醫「拉上病床強吻」!護理師值大夜班遇襲 事後繼續上班…反被傳成自願
死蟾蜍是我們某科的醫師,自己也是菜鳥卻愛「裝B」,更討厭的是總認為自己「下流是風流,低級當有趣」,三不五時來言語騷擾我們,尤其是對學妹「棠棠」。

貼所長爭博班名額!女學生向男友淚控「被性侵」 真相讓他綠得發光
那個年代,「博士學歷」比現在來得高尚有價值,而當年畢業班上就有兩位學生想考博士班,但打聽一下知道部分名額已經被內定走了,剩下一位名額可以搶。

花葬送「愛花老妻」最後一程 她走後夫種出整片花園:我下輩子也愛妳
雖然花園的主人只剩下一個,但花兒被照料的用心程度沒有被打折。蔡伯伯一株一株的告訴我,什麼月分哪一盆花會開、哪一株花差點枯萎又被救了回來、哪些是老奶奶生前的最愛,他一一的跟我介紹。這片花園對他來說是生活的重心,也是延續他跟老奶奶的感情。

93歲榮民爺病危送醫「身邊只剩長照員」 月花9K租老舊蟻窩仍感恩:有地方住就很好
張伯伯租在台北一處老舊公寓裡,空間小到光兩個人坐在房間就塞滿了,四周塞滿雜物和吃到一半的食物。「沒有人願意把房子租給我們這種人,房東願意給我地方住就感謝了。」

黑影空中亂竄「畫筆甩滿地」!壁畫師嚇閃尿 轉頭看見本體…拳頭硬了
有次他透過關係,接到台灣中部一間學校「美化走廊」的案子,雖然層層關卡下來,到手的錢變很薄,但這案子算是還一位前輩的人情,算一算沒虧就接了。

記者訪完廢墟「背後卡長角的妖」 弄清真相嘆:難怪《還願》到處上演
充滿濃厚民俗味的遊戲《還願》,最讓玩家印象深刻的,恐怕是何老師供奉的「慈孤觀音」,進而延伸出悲痛的杜家慘案。但遊戲之外,類似的悲劇天天上演。

壁畫師畫整牆「淡水夕照」 老人站2天全程看完 哽咽:我就在這長大
基本上,有人站在後面就算沒開口說話,多少就有壓力,工作起來也不太自在,但公共空間也不能趕人走,所以就盡量沉浸在自己的作畫世界,但有一次我遇到一位,令我印象深刻的「監督者」。

印小三照片「插圖釘埋陰廟」!正宮天天夢「群鬼圍攻撕肉」 痛醒後…身上滿滿瘀青
她說幾乎每晚都做同樣的惡夢,夢中有一群孤魂野鬼會來索命,她一直跑,但還是被團團圍住,眾鬼開始撕裂她的身體,最後是痛到醒來。醒來之後燈一開,身體莫名會出現大片的瘀青。

最危險尬聊!正宮小三坐隔壁「聊同個男人」:好巧喔他也送我這個包包
女人一生扮演的角色實在太多,但能訴說心事的人實在太少,所以一小時的美髮時間,我們就成了「髮型設計師」兼「心理諮商師」。最常見婆媳問題,偏偏婆媳都會來我們這邊洗頭,所以這邊聽聽那邊笑笑成了基本技能。

「妳牡羊性慾很強齁」噁男剪髮伸鹹豬手 設計師一句嗆到他縮回去
目前在台北一間連鎖美髮店,擔任各家分店的「技術指導」,偶爾會支援幫忙剪髮,這一做就是八年,遇過的客人不少,討厭的客人不少,但痛恨的只有一個,就是出沒在台北松山店的「色老頭」。

憂鬱男要剃光頭「反正不想活了」 暖心設計師「陪聊30分」拉他一把
事情發生在兩年前,此時一位男客人打破這平靜的夜晚。約莫40多歲,穿著拖鞋黑衣黑褲隨便的打扮,瀏海長到遮住眼睛,像隻古代牧羊犬,姑且叫他阿牧。

2男1女指定刺「甲乙丙丁」在身上! 背後原因刺青師也鼻酸:不想忘了「他」
好比之前有個男的,刺了一個英文名字在腳底,我覺得很奇怪不過沒問,後來聽他朋友說才知道:「哈哈哈,那是他情婦的名字啦。」好險沒問。

「受不了哭鬧」最常觸發虐兒!諮商師提兩大「腦內存款」 新手爸媽快筆記
很多時候,生活中繁瑣的雜事就夠折騰人,小孩的哭鬧不過是那根稻草,研究發現兒虐致死案中,以「小孩哭鬧」的原因最多,其次是「如廁問題」,「不適當照顧者」、「管教致死與爭吵」等。

帥Gay顏值太優「女人緣好到困擾」想斬桃花 法師苦笑:真想幫你承擔
看到他的第一眼,就是長得高、又帥且陽光的型男。這樣的先天條件自然吸引很多女人靠近,但對他而言這是困擾,想要的是男人,來最多的卻是女人。聽到這樣的困擾,做老師的還真想替他分攤。

受夠小王糾纏斬桃花!法師「斬情柴刀」一劈…他一周後車禍命危
首先,「好與壞」的定義每個人不同,我覺得明日花很好,但我老婆覺得她很壞;二來,有些你現在認為的爛桃花,之後可能轉為好桃花,多少愛情電影的套路,一開始男女主角互看不順眼,最後還不是到同張床滾床單。